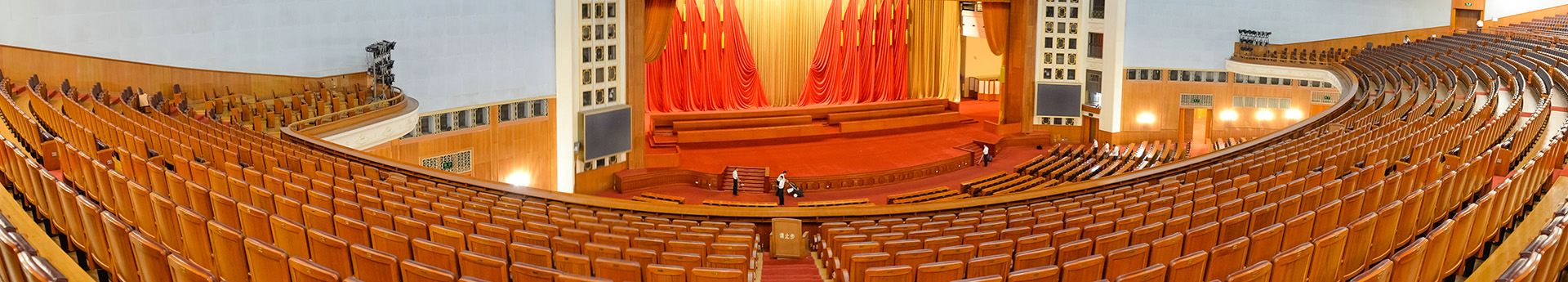一场未签字的合同与单位犯罪的博弈:从工厂流水线到法庭焦点的转折
在法律圈里摸爬滚打这些年,我见过不少案子,但2024年那起单位犯罪的纠纷,总让我觉得像一场没剧本的戏,既紧张又耐人寻味。主角是老周,一个小工厂的老板,50岁出头,靠生产零件养活一家老小。他怎么也没想到,一份没签字的合同,会把他的厂子和自己推上法庭的被告席。这故事里有生意的无奈,也有法律的冷峻,读来让人唏嘘不已。
开端:合同的漏洞
老周的工厂不大,十几号工人,专做汽车配件,靠着几家老客户吃饭。2024年春天,一个自称是大公司采购的家伙找到他,说要订一批零件,价值300万。老周乐开了花,赶紧备料生产。对方拿来一份合同,条款写得密密麻麻,说是先付30万定金,货到再结尾款。老周瞅了一眼,觉得没啥问题,可签字时对方说:“我们领导出差,回头补签,你先干着吧。”老周信了,收了钱就开工。
零件刚出厂一半,麻烦来了。那家公司突然联系不上,定金的30万却被查出是“赃款”,来源是一家被挪用公款的企业。警方找上门,说老周的工厂涉嫌单位犯罪,帮人洗钱。老周傻了眼:“我就是个干活的,怎么就犯罪了?”
危机:从老板到被告
老周被传唤时,正在车间盯着流水线。他跟警察喊冤:“我连客户面都没见过,钱是他们主动转的!”可证据不饶人:银行流水显示30万进了工厂账户,零件也真生产了。《刑法》第31条规定,单位犯罪是公司为谋取非法利益,经负责人同意实施的违法行为,单位和个人都得担责。检方认定,老周明知合同没签字还收钱,等于“明知故犯”。
我接手这案子时,老周已经被调查了半个月。他坐在会见室,满脸憔悴:“我哪知道钱有问题?我还赔了材料费呢!”我翻卷宗,心里直犯嘀咕。那份合同没签字,法律效力存疑,可老周收了钱又干活,确实给了检方口实。这案子得从源头挖真相。
交锋:证据的拉锯
我先从那30万查起。银行记录显示,钱是从个空壳公司转来的,背后牵涉一桩挪用公款案。我问老周:“你没核实对方身份?”他摇头:“他们说得头头是道,我信了。”我又找到工厂的会计,她说老周把30万全投进了生产,没一分私用。
庭审前,我跑去那家“采购公司”的注册地,发现早人去楼空。我还调了老周和对方的通话记录,对方催货催得急,不像要跑路的骗子。我把这些拼起来,证明老周是被蒙在鼓里的“工具人”。可检察院不买账,说老周没尽到审查义务,工厂的行为客观上帮了犯罪团伙。
庭审那天,法庭里挤满了老周的工人。检察官拿着一堆流水单,质问:“你一个老板,连合同都不签就收钱?”老周涨红了脸:“我怕丢了生意!”我当庭递上生产记录和通话录音,反问:“我当事人赔了本,哪来的非法利益?”我还请了个供应商作证,说老周订料时急得满头汗,不像洗钱的。
高潮:转机的曙光
关键时刻,警方抓到一个中间人,供认是他伪造身份,哄老周接单,30万是他故意转过去的,想用工厂洗钱。法庭上,这供词像根救命稻草。法官听完,宣布休庭。一周后,判决下来:老周和工厂无罪,案件另行追查主犯。
老周走出法庭那天,天空阴沉沉的。他握着我的手,眼泪差点掉下来:“我以为厂子没了,家也完了。”我拍拍他的肩,没多说。那30万没追回来,零件也卖不出去,可他保住了清白。
尾声:信任的代价与法律的公道
老周后来缩了厂子规模,只接熟客的单子,说是不敢再碰“大生意”。我想起这案子,总觉得单位犯罪的红线,像个看不见的网,老周差点被罩进去。那份未签字的合同,像个无形的陷阱,差点毁了他半辈子心血,却也在法律的严苛里,给了他喘息的机会。
这故事没英雄,只有个普通人,在生意的夹缝里,靠着点运气和证据,逃过了牢狱之灾。我做律师这些年,最怕的是看不清真相,最庆幸的是帮对了人。老周还在干厂子,听说每次签合同,都多看几眼对方的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