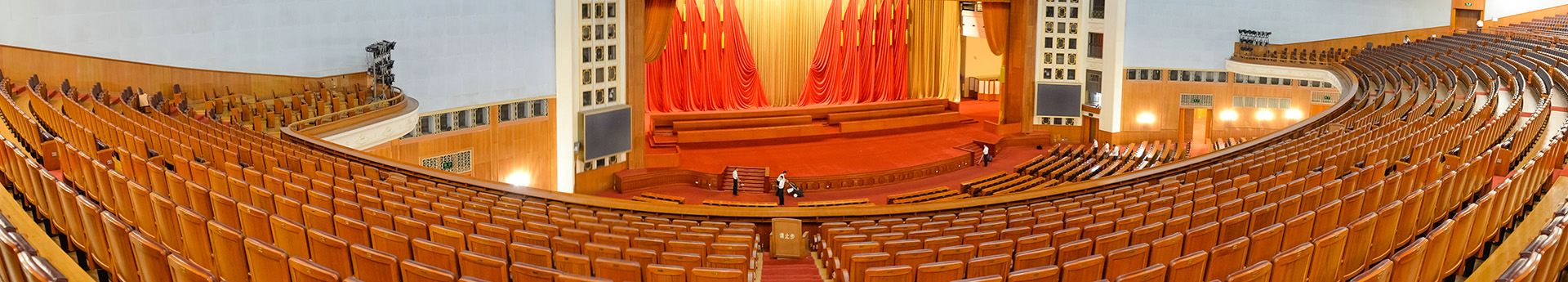一场失控的合伙生意与共同犯罪的纠葛:从兄弟义气到法庭裂痕的代价
在法律圈里混了这些年,我见过不少案子,但2024年那起共同犯罪的纠纷,总让我觉得像一出没彩排的悲剧。主角是老陈,一个40多岁的装修工,和他的发小阿明,因为一次合伙生意,从兄弟变成了被告。这故事里有义气的冲动,也有法律的冷眼,读来让人既感慨又唏嘘。
开端:合伙的诱惑
老陈干装修十几年,手艺扎实,靠口碑吃饭。阿明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兄弟,嘴皮子利索,常年在外跑点小买卖。2024年初,阿明找到老陈,说有个大活儿:一家新开的酒店要装修,预算200万,只要他们合伙干,利润能分一半。老陈一听,动了心。他掏出积蓄50万,阿明说自己拉客户、出主意,俩人一拍即合,没签合同,全凭一句“兄弟之间信得过”。
活儿干了一半,酒店老板付了100万进度款,老陈忙着带工人赶工,阿明管账。谁知没几天,老板报警,说钱被挪用了,装修材料压根没买齐。警方顺着账目一查,100万里有80万进了阿明的个人账户,再转出去不知去向。老陈和阿明双双被抓,罪名是共同诈骗。
危机:从兄弟到共犯
老陈被抓时,正在工地搬砖,满脸灰尘。他跟警察喊冤:“我一分钱没拿,全是阿明管的!”可证据不饶人:银行流水显示钱从公司账户转到阿明那儿,老陈是合伙人,签过付款单。《刑法》第25条规定,共同犯罪得有共同故意和行为,检方认定,老陈明知阿明乱搞账目,还配合他干活,等于“分工协作”。
我接手这案子时,老陈已经被羁押了半个月。会见室里,他抓着我的手,急得满头汗:“我真不知道他挪钱,我还等着分利润呢!”我翻卷宗,心里直犯嘀咕。阿明的供词把老陈咬得死死的,说老陈“早就知道钱不干净”,可老陈连账本都没摸过,这案子得从头理清。
交锋:真相的拉锯
我先从钱的下落查起。银行记录显示,那80万被阿明转给了一个“建材商”,可对方是个空壳公司。我问老陈:“你见过这个老板吗?”他摇头,说材料都是阿明联系的,他只管干活。我又调了俩人的通话记录,老陈几次问进度款的事,阿明都敷衍过去,没提挪用。
庭审前,我找到酒店老板,他说阿明一开始就承诺“低价高质”,可材料送来的全是次品,老陈还蒙在鼓里。我把这些线索拼起来,证明老陈没参与诈骗。可检察院不松口,说老陈作为合伙人,没尽到监管责任,等于“放任犯罪”。
庭审那天,法庭里气氛紧得像要炸。检察官拿出一堆转账单,质问老陈:“你连账都不看,哪来的信任?”老陈涨红了脸:“他是兄弟,我信他!”我当庭递上材料单和老板证词,反问:“我当事人一分钱没拿,哪来的共同故意?”我还请了个工人出庭,说老陈天天在工地干到半夜,不像骗子。
高潮:判决的分水岭
关键时刻,阿明在法庭上改了口供。他说挪钱是他一人干的,老陈不知情,只是被他哄着干活。法官听完,沉默了一会儿,最终判决:阿明诈骗罪成立,判了六年;老陈证据不足,无罪释放。散庭后,老陈坐在台阶上,低声说:“我这50万没了,兄弟也没了。”
我拍拍他的肩,没说话。那80万追不回来,老陈的信任也碎了一地。
尾声:义气的代价与法律的底线
老陈后来回了老家,干点散活儿,说是不敢再合伙做生意。我想起这案子,总觉得共同犯罪的认定,像把无形的刀,划开了兄弟情,也划出了法律的红线。法律是严肃的,它不看你信不信,只看你干没干。而老陈的故事,像个教训,提醒着我,也提醒着每一个普通人:义气再重,也扛不住法庭上那冷冰冰的证据。
这案子没英雄,只有个老实人,在生活的坑里摔了一跤,又靠着点真相和运气,爬了出来。我做律师这些年,最怕的是看不清人,最庆幸的是帮对了人。老陈还在干装修,听说每次接活儿,都多问一句钱从哪儿来。